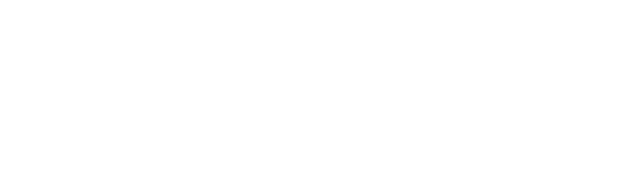“你们再这样不听劝,那地别种菜了,弄成花园吧”,我在电话里有些气急败坏,实在是觉得这两位老年人有些任性了,种块地把腰闪了。
一块地,七八十平米的样子,上面搭建了一个二十平米的阳光房,剩下的地被父母种上了几样蔬菜。当初买房时,母亲把整个镇逛了一个遍,就为房前有一块地,这个近乎有房子一大半面积的地让母亲心满意足,推窗可见绿,出门可踩地,我从母亲的笑容里感知着惬意,田园式的生活仿佛触手可及。
土地四周是木板围成的篱笆,本色,将一个院子装饰出简单平和的心情,篱笆墙低矮,一同站立的还有一圈葱茏的绿竹,相对于别的院子伸出墙头的花朵,母亲的这方小院有一种淡淡的静,每年能喧闹一下的可能就是那几畦菜地的丰收时节,以及那两棵蜡梅树和桂花树的花开时节。
父母大部分时间住在市里,我以为那块地大多时候是属于沉寂的。虽然少有照料,每个时节,父亲和母亲都按时去种上果蔬苗,很简单的种植,土地没有修饰,和从前的土地一样原始粗糙。
记忆里有一块地,在模糊的夜色里,一盏灯的光撑破夜的黑,忙完一天教学的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妹在自留地种豆。母亲在前面刨坑,我负责丢豌豆种子,姐姐跟在后面撒肥料,妹妹提着灯照亮。土地坑坑洼洼,让脚步高低不平,这样的土地没有给我一丝喜爱,我与土地最近的距离定格在那个夜晚,有些生冷。
这块地,同样没有给我一丝波澜。父亲母亲不需要再事无巨细地操心我们,如果这能让他们有些寄托,打发时光,算是我给这块地定义的使命了。
番茄、辣椒、蒜苗、芹菜、小白菜、青菜、豆腐菜、莴苣、卷心菜、萝卜、丝瓜……还有一种叫做狗儿豆的豆类,都被父母如期投放到土里,肥料是母亲用淘米水加瓜果皮、过期的酸奶之类浸泡而成,效果明不明显不清楚,但是土地如期长出一些蔬菜,有时繁盛有时零星,母亲和父亲总结着蔬菜没长好的缘由,商量着下一季的计划。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念念不忘地要种地,父亲十多岁入伍之后便离开了乡村的土地,母亲上山下乡时去的农村,后来也回了城,什么样的情愫让他们牵扯不舍呢?尽管每一次收割都不尽如人意,母亲总把收成分成三份带回来,一家一份,有时候同友人一起去镇上看风景,也会享受那块地长出的喜悦。
母亲不小心摔了腰,休息调养了几个月,那块地便闲置了起来,她总是放心不下,便安排我和姐姐去把菜园子打理一下。
推开院子的木门,一股草地的气息扑面而来,那块种蔬菜并不旺盛的土地长满了荒草,最高的齐腰了,我以为沉寂的土地其实并不沉寂,它在自己的岁月里狂热地与生命同在。桂花树下围满了一圈浓密的鱼腥草,有的开出了花,这让我眼前亮了起来,现在能在市场上买到野生的鱼腥草几乎无望,而像我这样一个对它无比钟爱的人,简直如获至宝。我突然觉得这块地无比神奇,它好像知道你想要的东西,即使没有眷顾,仍倾其所有,我在这块地面前的欣喜,唤醒了儿时模糊的记忆,有那么一条田埂,有那么一些零星的鱼腥草,有个小小的身影,有那么些简单的快乐。我眼前的土地温暖起来,爱来得简洁又迅速,土地也是聪慧的呀,它懂得人间,只是不语。我在一刹那仿佛也懂得了父亲母亲,他们投下一粒种子时的期待,应该是果实成熟时送到我们手中的幸福,土地不仅种出了希望,还生长着情感,它还是一个载体,传递着温情。
清理了杂草,还原了之前清爽的模样,在那个天气晴好的下午,坐在阳光房的窗台上,土地在我脚下,散发着青草香,淡如烟浓如酒,飘进我沏好的茶里,桂花树和蜡梅树两两相望,它们会在不远的时间里相继绽放,也会洒落一地馨香,交付于土地。我仿佛看见一场对话,关于岁月,关于爱。我俯下身,听见土地的声音:我哪里有什么使命,我只是热爱生命。
给母亲拍了视频发过去,看见一朵笑,开在岁月的藤蔓上,满是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