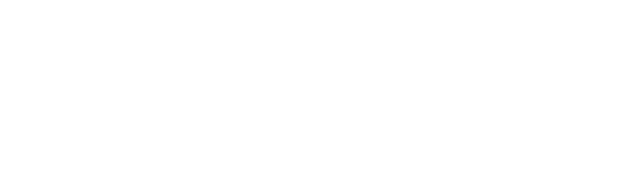从三亚回来,父亲捡几件贝壳带回家
置于窗台。他说,那是离别时大海的叮嘱。
它们按秩序排列,像已预知自己颠沛的命运
坦然接受一切久远的磨损。月光沿着
粗糙的花纹,审视它复杂的言语
贝类选择安静地保守秘密。
夜寐之时,我曾听闻海潮从它们口中吐出
裹挟缄默的鱼群,落日的神秘拜访
我羡慕那海底轻盈自由的海草。
想起老家一些逝去的人,一排老去的屋
像窗台的贝壳,心底的柔软
遗落在某场台风、某处暴雨。于是
我们把冷漠、诋毁与怠惰归咎于
海的无垠,直到多年后潮落,又一位老人
颤巍巍地拾起他钙化的往事。
瓷碗
我仿佛看见
多年以前,在声声吆喝的日夜
工匠们用沟壑纵横的双手
把平凡的泥巴揉出华贵的模样
瓷碗素白明亮,恍如家乡的月光
将他们尘微的一生
映照在时代的角落
多年以后,燕子落足春的檐下
黄墙青苔,一段细雨乐律
波动泥土的画笔
农人挥舞锄头,汗水在背后生芽
它在炊烟袅袅的土灶上
盛满农人一年的丰饶
后来,我们围在它身旁
研究它深藏的不凡
博物馆里人声鼎沸,瓷碗静谧如初
素白净亮,宛如一朵白莲
在历史长河里满载思绪
我们置身其中,化作一粒微小的水珠
孕育新的花苞
墙
走过那些我们所称赞的事物,眼见
宽慰的晚风,从遍布于身体的缝隙里
呼啸而出,而后被人与人之间
拙劣的猜忌层层阻碍。但一切都太晚
世间降下苦愁的雨,足以淹没
撕裂的雀鸣,使我们之间过剩的
自我意识,始终溃败于乞力马扎罗
被雪覆盖的裸露坦白,以致赤道的象群
被迫进行一场冬季的迁徙。
我们用棉草装填感性的洞窟
用毛发与落叶藏匿野性的躯体
沙砾打磨出光滑如镜的原野,聚集
一滴滴湖泊透彻的眼泪。回到我们
与城市最初的躯壳,用一把土
轻易地筑起一截隔阂之墙,将我们
分隔成无数细碎的河流。
我知道,有些事情正在悄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