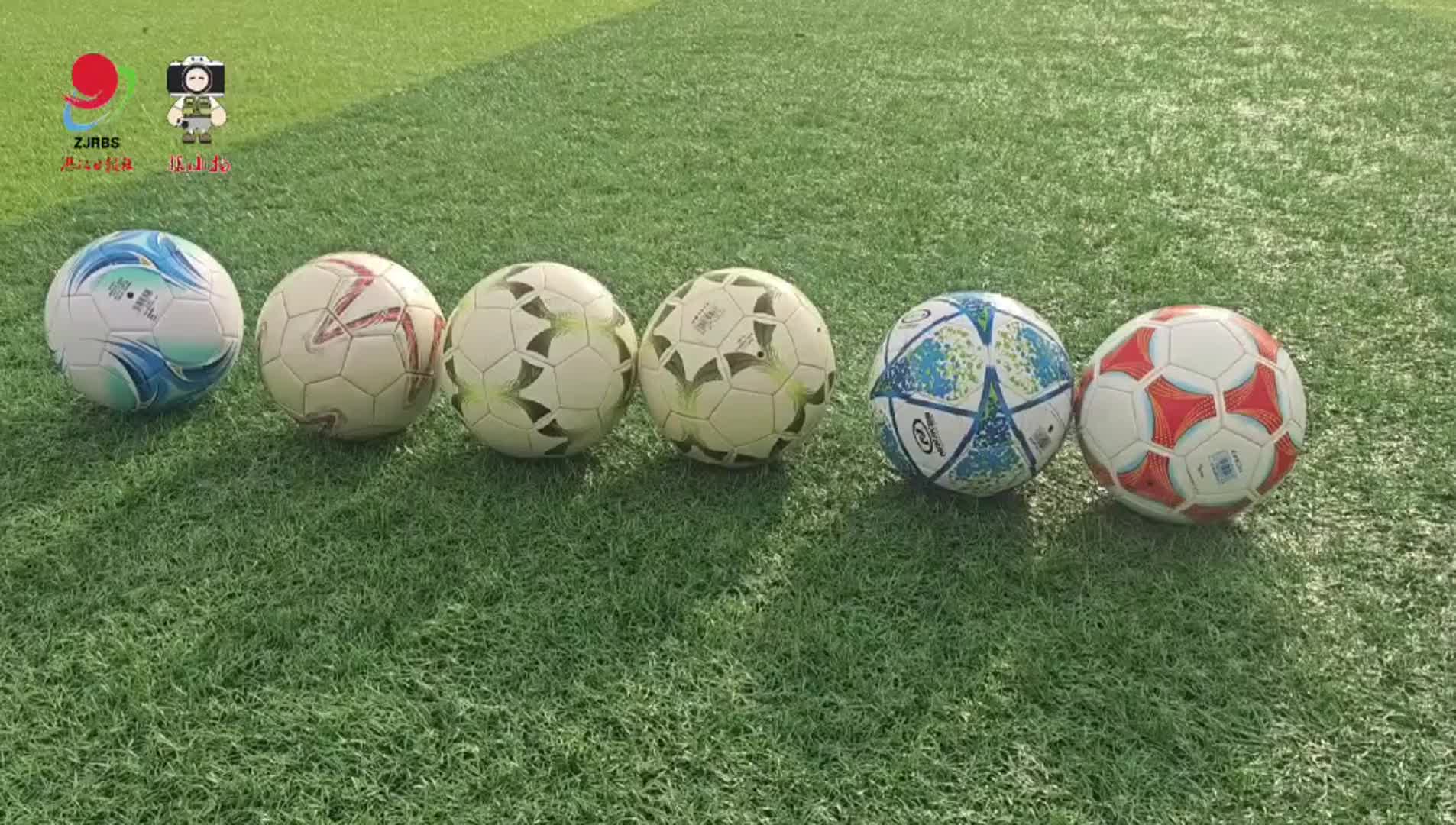母亲历来爱看木偶戏,那种边舞木偶边唱戏文的表演更是母亲的挚爱。也难怪,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除了白天出工劳动,晚上就是集中在队屋面前的晒谷场上记工分、听队长读报纸,女人们要么在煤油灯下缝衣服、织袜子、纳鞋底,要么就悄悄的讲些家长里短,而我母亲,却爱躲到队屋里头,顶着夏天的闷热,拿把葵扇边摇边听六叔公在清唱木偶戏《薛仁贵征东》。尽管没有木偶在面前舞来舞去,单从唱词,母亲也知道唱的是薛仁贵身着白袍在东征高句丽时冲锋陷阵的内容,因为母亲已经多次看过、听过这些木偶戏的戏文了,甚至心血来潮时还可以哼上几句《穆桂英挂帅》了。
其实,自我懂事起,就知道木偶戏在乡下叫“鬼仔戏”,一个戏班才三四个人,全部家当就是两个木箱装着的木偶和锣、沙鼓、大钹等乐器。每次演出就是一个男人托着木偶在戏楼内手舞足蹈,咿咿呀呀,然后一个女的也举着木偶咿咿呀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只见到白鼻子舞了一下转回后台了,沙鼓“嘚嘚得”猛响,又出来一个大花脸,在翻跟斗,不久一个头戴凤冠的女木偶又出来婉转一通,我懵懵懂懂看不明白,所以就不大喜欢看这“鬼仔戏”。可母亲不同,她不单在村里看,甚至在漆黑的夏夜提着煤油灯跑到邻村去看。母亲爱看木偶戏的理由很简单:可以增加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对小孩教育启蒙。
记得多年前,乡下除了农忙时节的吆喝与闲时邻里间的家长里短,或者是某些特定的节日,便再难寻出别的热闹响动。日子一天天的总在平平淡淡中滑过,田野和村落似乎迷迷糊糊睡着了,只有风过树梢,才偶然拨动一下这无边的寂静。然而每每阴历七月,晒谷场传出木偶戏班要来唱戏的消息时,仿佛无波的水面被投入石子,整个村子就骤然活跃了起来,特别是母亲,早早就去自留地里割回番薯叶,备好猪潲水,目的就是为了看“鬼仔戏”。
那木偶戏班是夫妻档,他们曾是大队宣传队男女主角。那时我才十来岁,对白鼻子、大花脸不怎么感兴趣,我最爱的就是趁机向母亲讨要一枚五分的硬币,到货郎档那里买上一竹筒炒瓜子,邀约三五小伙伴退到角落边上一粒一粒分享。从来是一分钱都掰开用的母亲,此刻为了能专心看戏,竟然毫不推辞!锣鼓声叮当铿锵,喧嚣中母亲眼神专注,静静在听,生怕漏听了哪句经典唱词。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最爱看的木偶戏是《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戏台上那刘氏被赶出家门,栖身寺庙旁的破窑洞,靠乞讨、纺织和寺庙接济度日,甚至变卖首饰换取书籍,仍坚持让儿子吕蒙正在寒窑孤灯下苦读,最终拜相成名的剧情,每每令母亲心情澎湃,激动不已,终于知道贫穷家庭也可以凭借读书实现阶层的跨越。那时我就好奇,母亲大字不识,记工员有没有记工分她都看不明白,为何却似乎格外懂这戏里滋味。
我初中毕业,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平时不怎么读书的我早早作好躬耕田亩的准备,因为,我清楚自己的家底,历来超支贫穷,好不容易有一个劳动力补充。但母亲坚决要我读高中,说不定通过寒窗苦读将来能谋个好前程。母亲对我说:“吕蒙正缺衣少吃,穷得叮当响,时常遭人白眼,可人家有骨气,坚持寒窑苦读,硬是通过读书高中状元,逆袭人生。”母亲的话,像黑夜里闪着油灯一样的光,映照着我少年迷茫的脸——那光,仿佛一粒种子,悄悄落在我的心田。
岁月如梭,转眼几十年。如今,当静夜降临,自己端坐在明窗净几旁,吹着凉风,品着香茗,看窗外城市不灭的灯火,读吕蒙正的《寒窑赋》,才知道吕蒙正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书生宰相,更是通过读书走上宰相之路的标志性人物。字里行间吕蒙正那股历经风霜的豁达与坚韧,掀起了内心深处的波澜——我蓦然想起当年晒谷场上母亲看木偶戏专注的眼神,想起她曾经给我的启蒙教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信就看吕蒙正”。母亲虽目不识丁,但却识得人间至理:贫瘠岁月里,人非但需活下去,还需借着故事里那些高贵的灵魂活出光亮,更要为儿辈指一条明路。
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爱看木偶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