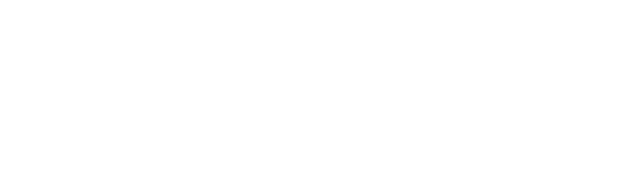夏夜的闷热,像一块浸透了水的厚布,沉沉地裹在身上。人刚静下来,那恼人的“嗡嗡”声便贴着耳根钻进来。随后,一支支细小的探针,开始在皮肤上寻找落脚点。
电蚊香液散发着微弱的红光,悠悠地弥漫出一丝带有化学气息的甜香。它虽也驱蚊,但总感觉少了些与暑气抗衡的真切感。这让我想起祖母的针线笸箩里,那些个用碎花布头缝制的小香囊,以及那些被艾草清香浸透的童年夏夜。
那会儿的驱蚊,是看得见、闻得着、带着泥土草木气息的。我的驱蚊香囊,从来不是现成买来的精巧玩意儿,而是祖母指尖流淌的智慧。她总在端午前后,翻捡出积攒的药材:艾叶带着山野的辛烈,紫苏叶揉搓出醒脾的芬芳,丁香粒小而味浓,藿香薄荷则透着溪水般的清凉。她戴着老花镜,就着窗棂透进的天光,细细剪碎,再按着古方配伍。小儿娇嫩,便取艾叶、紫苏、丁香、藿香、薄荷、陈皮各一小撮,药性温和,重在固表驱邪;大人体壮,则添上几朵清热解毒的金银花,力道便足了些。那些被阳光晒得酥脆的草叶药末,在她粗糙的掌心沙沙作响,最终被小心翼翼地填入一个个用绸布角或旧手绢缝成的三角小袋里。针脚或许不够细密匀称,却缝进了日月的耐心和对家人的护佑。
新缝的香囊,药香最是浓烈扑鼻。祖母帮我系在衣襟上、手腕间,或是悬在床头帐角。那香气,初闻是艾草、紫苏混合的辛香,霸道地驱散蚊虫的觊觎;细嗅之下,又有薄荷、陈皮的清冽甘醇,丝丝缕缕钻入鼻息,竟也压下了几分心头的燥热。祖母说,这香气是活的,能顶半个月的光景。待那味道渐渐淡薄、散尽,就该换上新囊了。若是不巧被雨淋湿或汗水浸透,药力便泄得更快,祖母便又忙着拆换新药。
香囊虽好,但非人人相宜。怀了身孕的邻家婶婶,祖母是绝不给的。祖母告诫我:“芳香走窜,怕惊动了胎气,若有人闻了直打喷嚏,那便是与哪味药草无缘了。”
若论更简便的驱蚊法,灶台上的八角便是现成的法宝。取三五颗黝黑发亮的八角角瓣,丢进粗陶罐里,添几瓢井水,在灶上咕嘟咕嘟煮开。那浓烈奇异的味道,瞬间便霸占了整个灶房。待水色转深,晾温了,祖母便用这棕红色的八角水,蘸湿了粗布手巾,给我们擦洗胳膊腿脚。皮肤沾上这汤汁,起初是辛辣的微刺感,很快便留下一层无形的屏障。蚊虫嗅到这气息,竟也悻悻然绕道而行了。这法子土气,却像田埂边的野草,自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
如今,驱蚊不过是一键电钮的易事。灭蚊灯散发着幽幽蓝光,电蚊香片默默蒸腾,驱蚊液只需一喷,气味浓烈且起效迅速。它们高效又便捷,宛如一道无形的科技屏障,将恼人的蚊虫阻隔在外。
然而,当空调的冷风显得过于生硬,当化学制剂的气味在密闭空间中久久不散,记忆深处那混合着艾草、紫苏、八角辛香的夏夜气息,便会悄然浮现。
那气息里,有祖母低头缝制香囊时垂下的银发,有灶膛中柴火噼啪作响的余音,有井水擦身时的丝丝清凉,更有一种与草木自然相融的熨帖之感。它驱走的不仅是蚊虫,更是内心的浮躁;它采用的是天地的馈赠,守护的是人与万物之间那份古老、带着药草清芬的界限与默契。
如今,若腕间还能系上一枚手作的驱蚊香囊,那暗香浮动间,便不只是驱蚊的屏障,而是系住一段慢时光的绳结,留下一缕在钢筋水泥丛林里萦绕不去的、属于泥土和草木的悠然夏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