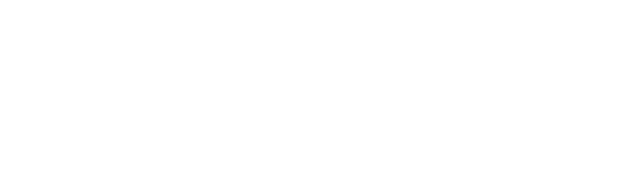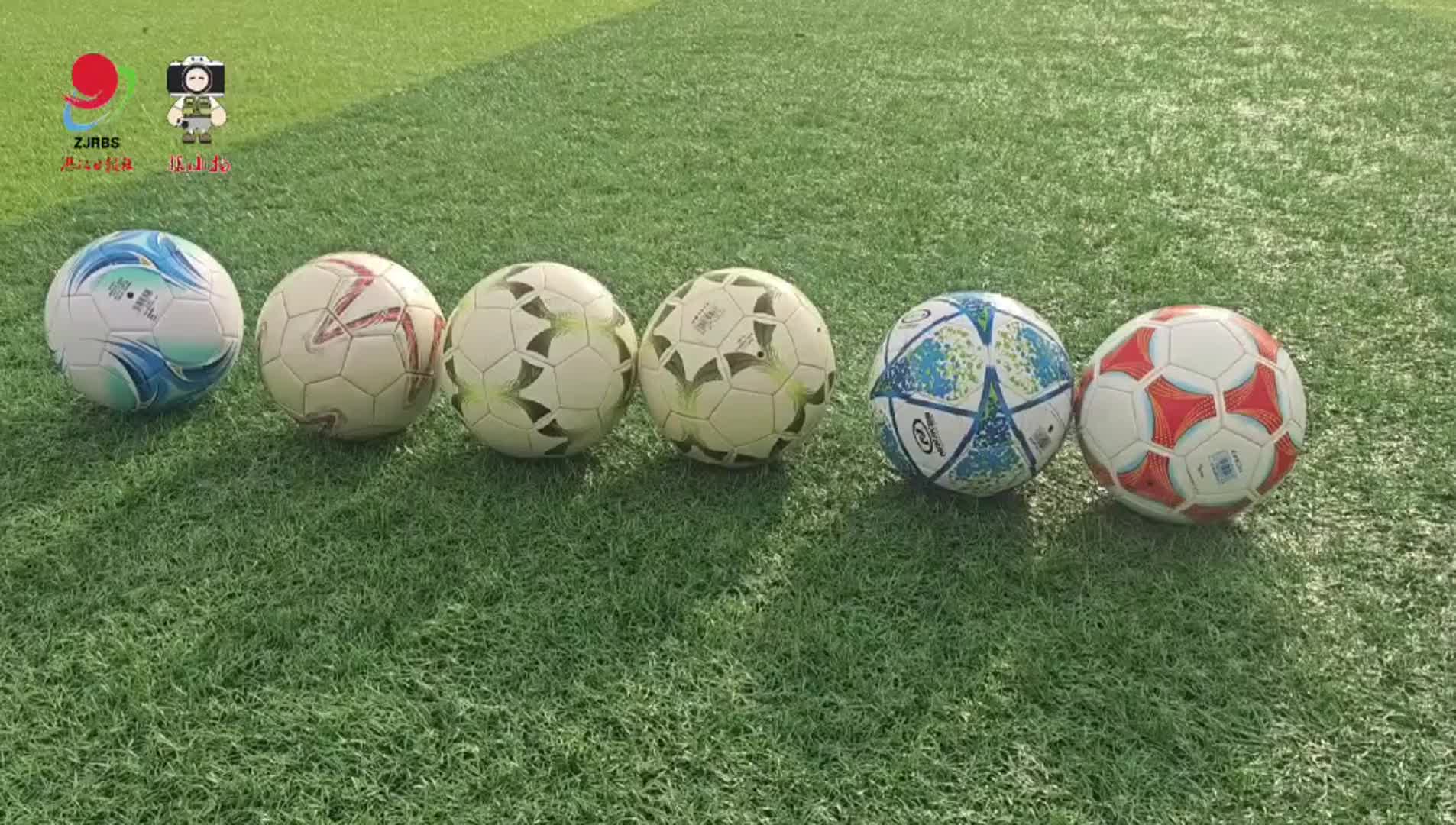一夜风雨过后,院子墙角的山稔子悄然熟了。紫黑色的果子把细枝压得弯弯的,果皮上还沾着没干透的雨珠,像刚从山涧里捞出来的野桑椹,紫得发乌,仿佛轻轻一碰就能捏出软绵的肉来。
我踩着积水走过去,指尖刚触到叶片,蓦然想起五年前海田花市老板把它塞给我时的模样——矮小的枝干上长着几片蔫黄的叶子,根部裹着的泥球干裂得能掰成碎块,树身发僵,毫无生气。那时,老板用塑料袋随便一裹,说这棵山稔树是从野外挖来的,估计养不活了,送我不妨试着养养看。
我那天去花市,本是为了挑一盆像样的年花,一眼看中的是蝴蝶兰,转身离开时,怀里已捧着它。
这盆蝴蝶兰是名贵品种,粉紫色的花瓣层层叠叠,像停驻的蝶翅,花梗被细细的铁杆撑着,裹着金箔纸,连花盆都是青瓷的,沉甸甸压在掌心。老板反复叮嘱:“不能晒强光,不能浇太多水,室温低于15度就得搬进屋。”我用旧毛衣裹住花盆,一路护着,生怕风吹着、冻着,连脚步都放轻了很多。
相比之下,这棵山稔树实在像一段多余的枯枝。回家后腾出手,我捏着它干瘪的枝条,随手按在墙角的砖缝里,土都没压实,转身就去侍弄蝴蝶兰了。那里常年照不到多少阳光,雨水好的时候会积起一汪浊水,旱季又裂开蛛网似的纹路。我从没想过要给它浇水施肥,甚至觉得它熬不过那个冬天。
头年春天,那盆蝴蝶兰成了院子里的主角。清晨,我搬它到室外晒太阳,正午怕晒狠了,又赶紧挪到树荫下遮阴;傍晚露水上来前,再轻手轻脚抱回屋里,垫在绒布托盘上。周末蹲在花架边,看见叶片上沾了点灰,就用棉签蘸着温水一片片擦;发现盆土表层干了,立刻用尖嘴壶沿盆边慢慢浇,生怕水流冲着根部。老板送的专用肥,我按说明掰了小半粒埋进土里,连埋的位置都离根须隔了寸许,怕烧着它。
即便这样,不出两个月,蝴蝶兰还是蔫了。粉紫色花瓣失去光泽,像被抽走水汽,软塌下来,边缘向内蜷成发皱的小卷,轻轻一碰就往下掉。盆底漏出的水带着股腐味,我扒开表层土发现,白胖的根须竟烂成褐色的丝,缠在青瓷盆壁上,像团泡坏的棉线。无奈把枯了的蝴蝶兰扔进垃圾桶时,我眼角扫过墙角——砖缝里那截“枯枝”仍像截枯木,只是干裂的皮缝里,藏着一抹淡淡的绿。那时正为蝴蝶兰心疼,只当是眼花,没往心里去。
日子跟着节气慢慢挪,秋深了又冬尽了,等院内的茶花抽出新梢时,春天已经站在了墙头。再看墙角,那棵山稔树竟然活出了些模样——开春时冒出的几点新绿,已经舒展成星星点点的嫩尖,像不小心撒在枯木上的星子。一天,我提着水壶给茶花浇水,路过墙角时特意停了步:新叶嫩得能掐出水,卷着边儿,像刚出生的雀儿蜷着翅膀。我愣了愣,终究没把水壶递过去,心想,这种野生东西,大概不需要浇水。
真正让我记住它的,是去年台风“摩羯”过境的那个夜晚。狂风卷着暴雨拍打着窗户,我躺在床上听着院外的响动,总觉得那些新栽的茶花要遭殃。第二天清晨风停了,推开院门果然看见一片狼藉:茶花的枝条断了大半,紫薇被连根拔起,唯有墙角的山稔树还立在那里。它的主干弯成了一张弓,几片嫩叶被撕碎在泥里,可根须却像铁爪似的嵌在砖缝深处,沾着湿漉漉的泥土,透着股不肯认输的劲儿。我蹲下来,指尖碰到砖缝里的湿土,见到它的根早钻出了泥球,顺着砖缝的裂纹往深处钻,像在石缝里织了张网。那天我蹲了很久,直到积水打湿裤脚,才慢慢站起身——原来有些生命,从不需要谁来证明它的存在。
这些年就这么悄悄过去,我有时在院子里停脚看着不起眼的山稔树。盛夏日头最毒的时候,它把叶片卷成小筒,边缘微微发焦,像攥紧的拳头,憋着股不松劲的气;到了深秋,冷霜打过来,叶子慢慢浸成赭红,比院外榄仁树的紫红叶子更沉些,风一吹簌簌响,倒像藏了片山野里的秋声。春天开花时,细碎的红白色小花藏在叶缝里,不香,也不惹眼,我却特意搬把小凳坐在旁边,看蜜蜂嗡嗡地来采蜜。
一天,外地朋友来作客,指着墙角那蓬越来越茂的绿影问:“这叫什么树?它倒有意思,枝干上还带着老伤呢。”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砖缝里钻出来的山稔树枝干,被挤得歪歪扭扭,皮上留着往年台风刮出的裂疤,却照样往上窜。“它是山稔树,也叫桃金娘,南方山野到处都是。”我说。
朋友伸手碰了碰叶片,指尖抚过疤痕,笑起来:“难怪这么泼实。野地里长起来的东西,哪用得着人天天盯着?你看它这枝干,磕磕绊绊的,倒比那些修得整齐的树有精气神。”
他说得没错。那些被我精心呵护的花草,像温室里的娇客,受不得半点委屈。浇水多了会烂根,日照少了会黄叶,稍不留意就香消玉殒。可这山稔树却像个倔强的山野孩子,给点阳光就拼命生长,遇上风雨就紧紧扎根,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活下去这件事上。它从没想过要开出多么艳丽的花,结出多么饱满的果,只是凭着一股子本能,在墙角的方寸之地扎下根去,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活出自己的姿态。
六月的湛江,雨总下得没个歇脚,前一场的水痕还在砖缝里发亮,风裹着新的雨珠又砸下来,把山稔树的枝叶摇得哗哗响。然而,墙角的山稔树,竟捧着满枝的果实站在那里:紫红色的稔子挤挤挨挨,任凭风雨使劲摇晃,蒂头依旧攥得紧紧的,偶有一两颗被吹落,在泥地里洇出点点殷红,剩下的依旧牢牢挂在枝头,像一串串被雨水洗亮的小灯笼。
我的目光落在那串最沉实的果子上,摘下一颗放进嘴里,果肉软绵,甜里裹着点青涩,在舌尖慢慢化开,带着阳光和泥土的味道。咀嚼时忽然想起五年前它干瘪的模样,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原来生命力从不是靠谁捧出来,而是靠自己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