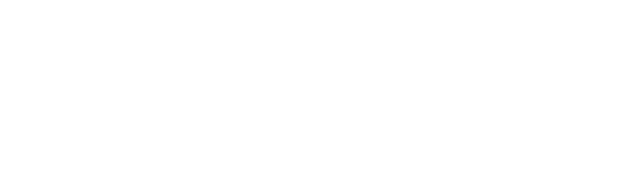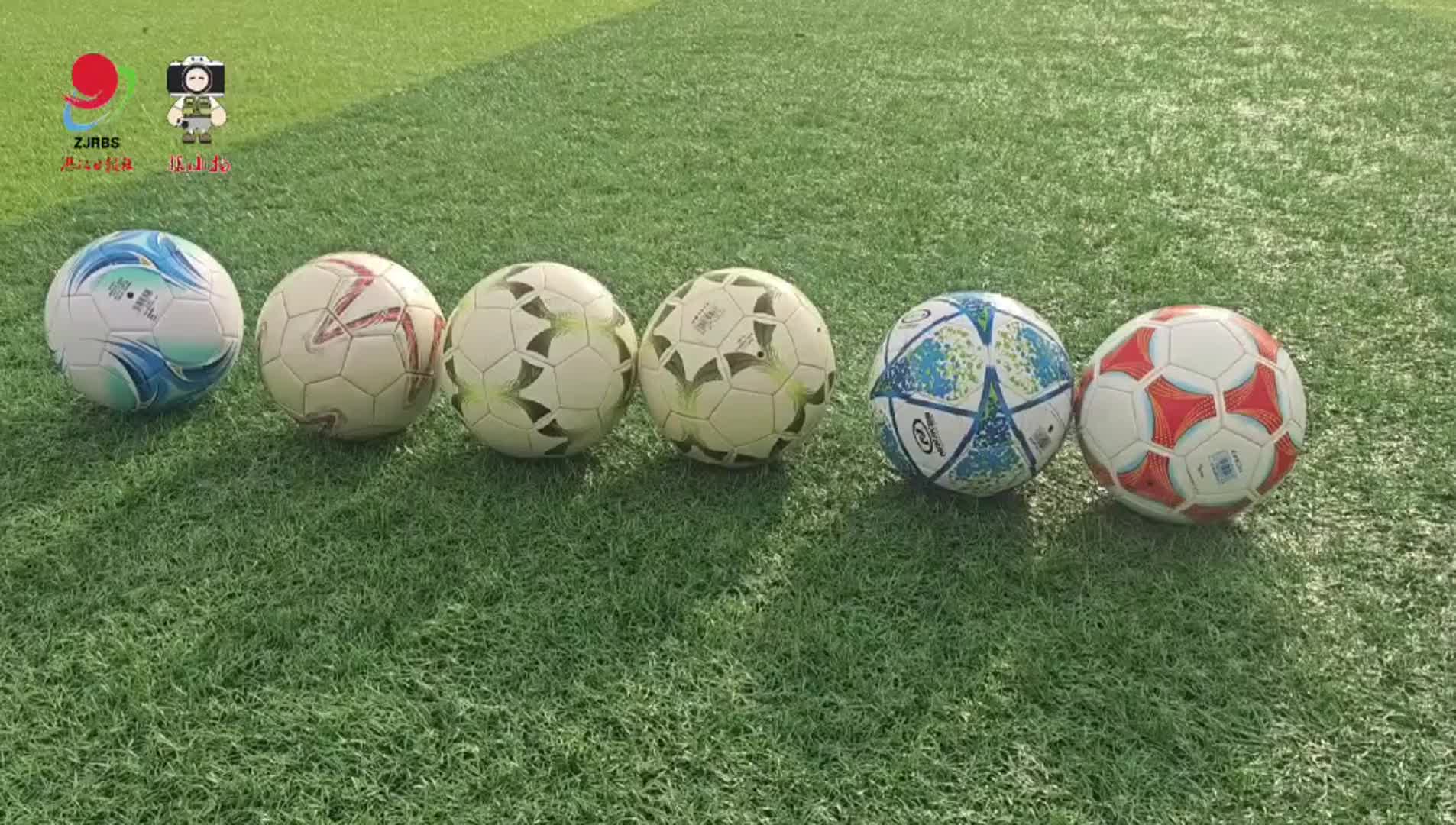我的书房窗外,有棵年岁不小的柿子树,树干已有碗口粗,树皮皴裂着,纹路深深浅浅,像老人手背上安静盘踞的青筋。
初搬来时是春天,它满树新叶,毛茸茸的绿着,并不惹眼。而后开花,小灯笼似的,藏在叶间,花色也是淡黄近白,羞怯怯的。那时我伏案劳形,目光难得在它身上停留。日子便这么一天天流过,像指间漏下的沙,无声无息。
直到这个秋日。
今晨推窗,一股清冽之气扑面,正撞见它最好的时节。夜来想必降了霜,此刻秋空碧蓝如洗,澄澈得像一块新拭的琉璃,便衬得满树一派斑斓。叶片经了霜,大半镀上浅黄淡金,边缘微微卷着,像古籍的书页,却仍有几片固执地绿着,是那种沉郁的、饱含水分的苍绿。再看那些果实,沉甸甸的,压弯了细细的枝,像一树悬着的小小磨盘。它们大多已转为暖融融的橙黄,瞧着便觉温软;偏偏蒂窝处,还恋恋不舍地留着些许青绿,像不愿完全褪去的少年意气。这般橙黄橘绿,参差交错,织成一片,比那全然的、火急火燎的红透,更耐看更有味,更合乎我这中年人的眼缘。
这静默的景致里,自有活泼泼的动趣。
白头鹎是这儿的常客,灰褐的身子灵巧地隐在枝叶间,只一动,便露出那圈雪白的头冠,一耸一耸。它挑个软熟的柿子,尖喙轻啄,浅尝辄止,很是斯文,仿佛在品一盏清茶。喜鹊便大不相同了,披着黑白分明的礼服,长尾一翘,踱步枝头,俨然是这里的主人。它侧着头,黑豆似的眼珠精明地打量一番,选中目标,便毫不客气地狠狠啄下去,直弄得汁液淋漓,染了满喙。我看它这般大快朵颐,也不嫌它贪嘴,反觉这偷来的一份生机,格外盎然。
最妙的,是那偶尔的“噗”一声,又轻又沉,像是饱嗝,又像是叹息。那是熟得再也挂不住的果实,终于辞别枝头,坦然地投入泥土的怀抱。这声响落在心上,不惊,反添一分幽寂的静。万物各有其时,强留不得,这道理,树比人懂。
看着这树,便不由得想到自己。
年轻时,大约只爱那满树火红,觉得那是圆满,是成功的极致象征。如今入秋之年,双鬓也见了霜色,反倒更懂得欣赏这青黄参半的景致了。那未尽的青绿,何尝不是一种沉淀下来的风骨?它提醒你,完全的甜熟或许意味着即将的腐烂与凋落,而这一点点恰到好处的生涩,恰是来日方长的底气,是生命厚度的见证。苏轼在杭州做官时,见初冬景致,曾写下“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想必领略的,也正是这般复杂的、不急于求成的人生滋味。那“橙黄橘绿”,说的哪里是物候,分明是一种境界。
夕阳西下,余晖漫过来,像稀释了的蜜糖,给柿子树、每一颗果,都细细镀了层柔和的金。那些橙的、黄的、绿的,此刻都融在这暖暖的光里,轮廓模糊起来,色彩交融起来,浑然一体,像一幅珍藏的、色泽温润的古典油画。
我静静立了半晌,轻轻掩窗,坐回书桌前。摊开那本未读完的书,提起那支惯用的笔,窗外的世界暂且隔开,心中却不似往日那般空茫,像是被那窗外的秋色给填满了。满满的,又是妥帖的、安宁的。这“橙黄橘绿时”,原是岁月看我耕耘半生,悄悄塞给我的一份厚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