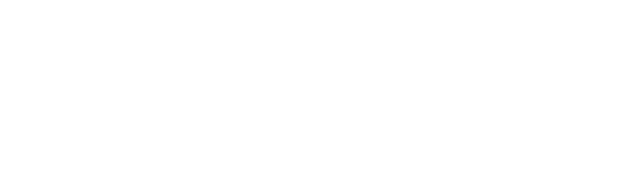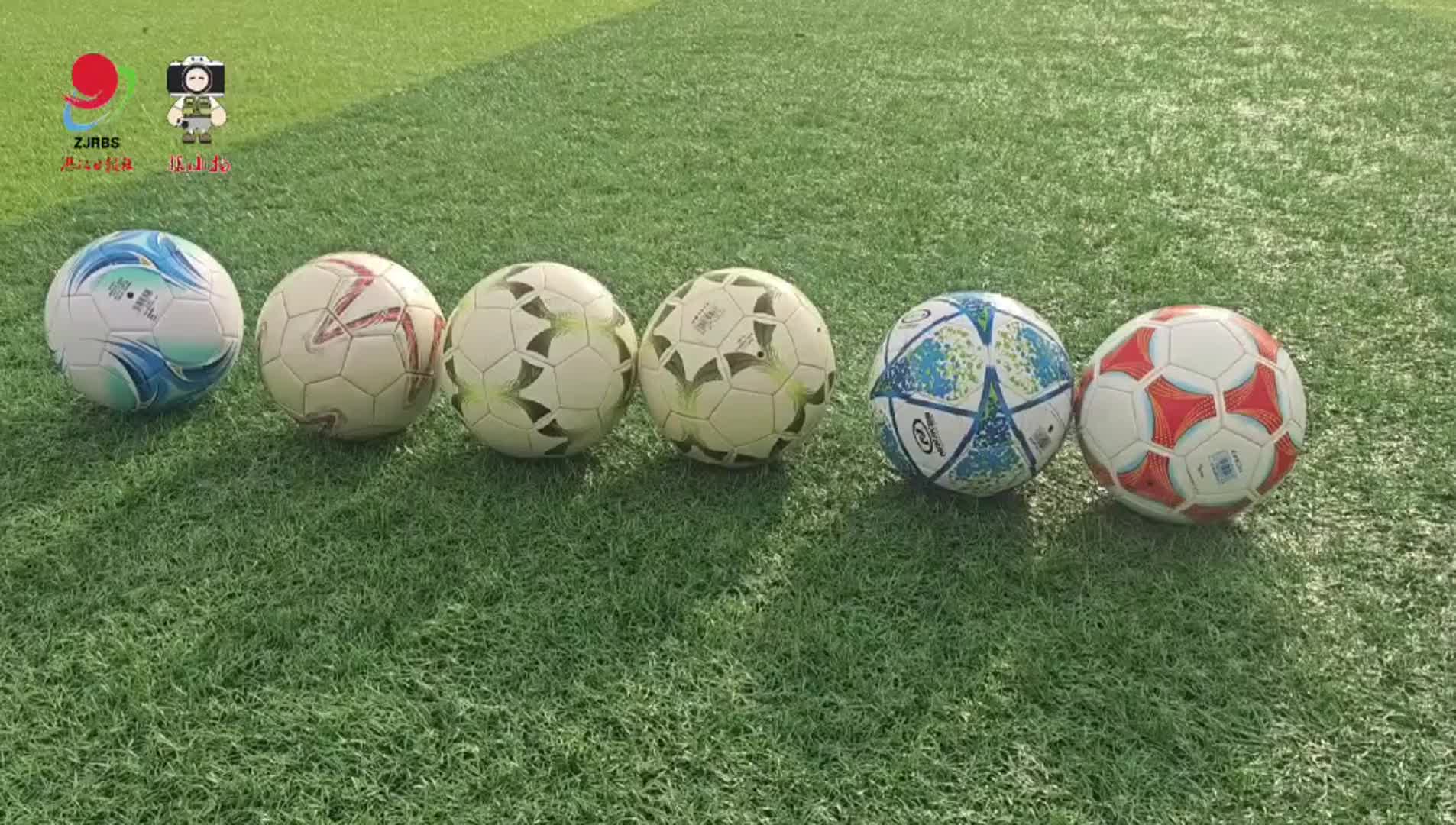窗边那台旧收音机,木头壳子磨得泛着蜜色的光。拧开开关,总要等上几秒,才听见里面“嗡”的一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醒过来。声音总带着沙沙的杂音,像春蚕啃桑叶,又像黄昏的细雨。
最爱在午后把它放在窗边,听戏曲频道播放咿咿呀呀的老戏。那声音朦朦胧胧的,带着毛边,像隔着一层温热的雾气。
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太阳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收音机里正唱着《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就在这当口,一阵风从窗外溜进来,带着味儿。
是豆花香。刚点好的、最鲜嫩的豆花。这味道清清淡淡的,却又执拗地往鼻子里钻。温润的豆香底下,垫着一丝石膏的清气,还有像揭开蒸笼时那股带着甜意的水汽。它安安分分的,带着朴素的、让人心安的暖意。
这味道一进来,就和收音机里的唱腔缠在了一起。那婉转的曲调忽然有了形状,有了温度——像一大勺颤巍巍、白嫩嫩的豆花,滑溜溜的,带着温吞的热气,从耳朵滑进心里,在那里暖烘烘地摊开。而豆花的香气,也被那老收音机镀上了一层昏黄的色泽,变得可以“听”见了,成了唱腔里悠长的拖腔,成了弦子底下轻柔的伴奏。
思绪一下子飘回很久以前,同样懒洋洋的下午。那时住在乡下外婆家,巷子口总有个挑担子的老伯,吆喝声沙哑绵长:“卖——豆——花——”我攥着几毛钱,端个大搪瓷碗跑出去。看他揭开木桶上厚厚的白棉布,更浓郁滚烫的豆花香“轰”地涌出,把人整个包裹。他舀豆花的动作很慢,豆花落入碗中像一大块洁白的云,微微颤动。淋上金黄的糖浆,甜香便和豆香圆满地融合。
捧着那碗热豆花站在巷口,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那种简单踏实的感觉,大概就是童年最确切的幸福。
收音机里的戏不知何时换成了新闻播报,字正腔圆的,把我从回忆里拽回来。窗外的豆花香也不知何时散去了。空气里又只剩下午后的阳光味道,和收音机永恒的沙沙声。
心里泛起一丝说不清的惆怅,像丢失了什么宝贝,又像做了场极短极真的梦。但我总觉得,豆花的香气并没有真正消失,它就藏在老收音机的每一个音符里,每一丝杂音的后面。往后每当听到这沙哑的声音,鼻尖总会隐隐地,再次嗅到那股温润的、朴素的暖香。
那些看似不相干的感觉,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悄打通,然后紧紧缠绕,再也分不开。旧收音机的声音,和记忆里的豆花香,于我,便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