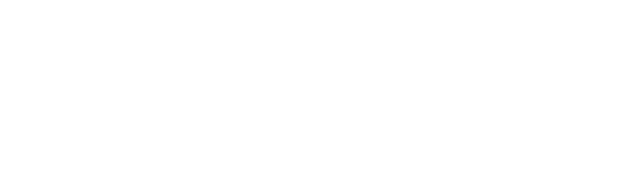在现代都市,年轻人或许从未听闻“瓦桁面豉”四字。它不像网红酱料般喧嚣登场,却如一缕幽微的炊烟,萦绕在乡村老一辈的记忆深处。
瓦桁面豉,实则乡间自制的面酱,得名于其独特的晾晒方式——旧时村落青瓦覆顶,一排排如鱼鳞般的瓦片层叠,行成“瓦桁”。乡人将酱料置于瓦桁上,任烈日与熏风激情碰撞,形成风味。它承载着物质匮乏年代里最醇厚的生活滋味,裹挟着我的温情记忆。
我儿时生活在农村。每逢盛夏,母亲总喜欢制作瓦桁面豉。
她挑选颗粒饱满的新鲜黄豆,用清水浸泡半日使其舒展筋骨。随后猛火煮水至沸腾,豆子入锅后先以大火煮,再转文火慢煨一小时。此时黄豆早已酥烂如泥,指尖轻捻即化。
灶膛柴火噼啪作响,铁锅蒸腾的热气模糊了母亲额角的汗珠。她擦一把汗后,将煮至绵软的黄豆与面粉揉成团,动作轻柔似在安抚婴孩——一斤黄豆配二两面粉。粉团被搓成长条,再用菜刀切成块,趁热倒入宽口瓦盆里。
接着是发酵。母亲将豆泥饼安放于竹编的簸箕中,覆上洁净纱布,静置暗处焗养两日。待掀开盖布,只见雪白菌丝如初春新芽般悄然爬满表面,然后将豆饼移至烈日下曝晒三四天,豆饼水分悄然蒸腾,体积收缩至半,质地变得酥脆可掰。此时需调制盐水:一斤清水兑入二两粗盐,浓度恰到好处。
最后一步曝晒才是重头戏:为防鸡犬啄食,母亲将盛满豆泥的陶盘端上瓦桁曝晒。骄阳与穿堂风成为最天然的发酵师,瓦桁的弧度恰成天然聚光镜,而青瓦吸热快、散热缓,使酱料受热均匀;熏风穿行瓦隙,带走湿气却不损风味。
那段时间,她每日清晨攀上竹梯,以竹筷顺时针搅动酱料,让每一粒豆泥均匀沐浴阳光,动作虔诚如僧侣转经;暮色四合时,她再攀上竹梯,把豆泥收入屋里,用纱布盖着。如此循环往复,月余,豆泥渐融为浓稠酱糊,豉香由隐微至馥郁,最终凝成琥珀色的“瓦桁面豉”。
面豉制成,便派上大用场。母亲取一勺深褐色的酱膏,或拌入薄切的五花肉,肉脂与酱香交融,蒸腾出琥珀色的油光;或与咸香的榄角同蒸,酸涩与醇厚在蒸汽中和平共处。
记得读高二住校那年,我将一瓶面豉蒸猪肉放在宿舍铁架床上,瓶盖掀开的刹那,咸鲜气息扑面而来。我小口啜食,肉粒裹着浓稠酱汁滑入喉间,先是咸鲜直击舌尖,继而豆香层层绽放,最后是猪肉的甘香弥漫。这复杂层次,是机器无法复制的生命律动。
香味在宿舍里弥漫。舍友们围拢过来,指尖蘸取酱汁轻尝,眼睛骤然发亮:“比食堂的肉还香!”我分出一勺,她们咂嘴回味,笑言“吃过返寻味”。
一瓶酱肉,我竟吃了五日,每口都像在咀嚼时光的馈赠,因我知道,酱肉的香气里有阳光的坦荡,有雨水的清冽,有时间的深邃,有母爱的缱绻。
如今,工业化酱料以标准化的鲜味席卷餐桌,乡村的瓦顶老屋渐被平顶楼房取代,瓦桁已不多见,手工晒酱的习俗亦如暮色般淡去。然而,当我在超市拿起一罐标着“古法酿造”的瓶装豆酱,却总觉少了什么——瓦顶烈日下的温度、母亲搅动酱料时臂弯的弧度、同学分享美食时眼里的亮度。瓦桁面豉的消逝,不仅是一种食物的退场,更是农耕文明中“慢智慧”的隐退——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我们是否遗忘了耐心等待?
前段时间,我回到乡村。父母过世后,老屋空置多年,破旧不堪。
我的目光抚过斑驳的瓦片,恍惚间又闻到面豉的醇香。它像在提醒我:有些滋味,须用时光慢酿;有些乡愁,唯有瓦片能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