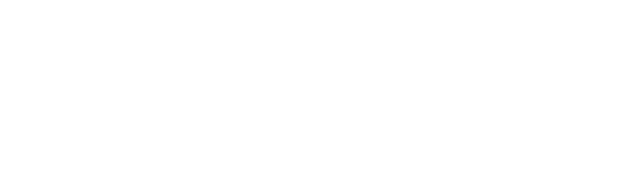深圳南头古城大门。
岭南的初冬总带着几分舍不得褪去的温润,风里少了深秋的燥意,多了层清洌的软,晨雾还没散尽时,深圳南头古城像被裹在半透明的白纱里,青砖缝里渗着的微凉,竟能把朝阳的和煦衬得愈发醇厚。
刚走到南头古城牌坊下,就见檐角落着几只寒鸦,黑羽沾着雾珠,“呀”的一声振翅飞走,翅尖扫过垂落的灯笼穗,把整座城晃得又软又暖。空气里飘着糖炒栗子的焦香,混着老木头的沉香与巷尾糖水的甜,吸一口都是熨帖的暖。
古城门口那棵老榕树该有上百岁了,枝丫斜斜地往城墙上探,叶片边缘染了浅黄,像给深绿缀了圈金边,疏影落在青石板上,叠成半个凉棚——石板缝里还凝着一层薄霜,太阳一照,化成细水珠往下渗,把磨得发亮的青砖润得更显温润。几个穿薄棉袄的老人摇着蒲扇坐在石凳上,竹凳腿陷在石板缝里,纹路里嵌着经年的落叶碎,倒像是长在那儿的。他们面前摆着粗陶茶罐,茶汁浓得发褐,热气裹着普洱的陈香往上飘,茶盅口沿结着层薄茶垢,跟城墙的斑驳纹络比着岁月痕迹的深厚。“靓仔,先歇歇脚嘞。”最边上戴布帽的老人抬抬手,从竹篮里捻出一片刚从巷尾摘的陈皮,果皮上的白霜蹭在我的手背上,凉得像块碎玉,又递来颗热乎乎的糖炒栗子:“刚从巷口买的,壳好剥,肉甜得很。”古城的待客礼从来不用客套,就这点带着陈香的清爽与栗子的暖,倒比温热的姜枣茶更解乏。
往里走时,石板路被暖阳晒得温温的,脚底板隔着帆布鞋都能感觉出那股从砖缝里透出来的暖,偶尔踩着没化尽的薄霜,还能听见“咯吱”一声轻响。转进窄巷就不同了,两侧骑楼的廊柱挤着往中间靠,木质的柱身上刻着深浅不一的纹路,是年月磨出的印记,把日头剪得只剩几缕碎光,落在青石板上,晃得像撒了把碎金。风穿堂而过时,带着巷尾糖水铺的雪梨川贝香,混着点井水的凉,还裹着隔壁汤圆店飘来的糯米甜香,绕着廊柱转了圈,才慢悠悠往深处去。
转去文氏祠时,廊下的石凳被树荫遮得正好,凳面凉丝丝的,却不刺骨——石缝里还凝着点薄霜,像撒了层碎盐。祠堂的木门漆皮掉了些,露出底下的木色,浅一道深一道,像本翻旧了的书,每道痕都是被日子磨出来的故事。檐下挂着的旧灯笼垂着穗子,穗子是绛红色的,被风一吹就轻轻晃动,扫过青砖地面时,沙沙响,像有人在低声念碑上的字,带着点说不清的绵长。有一位穿校服的学生趴在石阶上写生,铅笔尖在画纸上划拉,沙沙声混着风的轻响,把“人生自古谁无死”的碑刻描得方正,笔锋里透着一股认真,又把碑前开得正野的麦冬草描得软乎乎——草叶上沾着一点薄霜,泛着浅白,学生也仔细描了,说“这是古城的霜花,藏着冬天的心意”。
廊柱上爬着几丛爬山虎,叶子大半染成了暗红,像燃着的小火苗,却还犟着点绿,死死趴着柱身往上爬。有蚂蚁顺着藤蔓往上爬,爬几步停一停,许是被凉得慌,触角碰着叶片上的霜珠,倒像是在跟冬天打招呼。学生忽然抬头问我:“你看这祠堂的木梁,是不是像老榕树的枝?盘盘绕绕的,都藏着劲儿。”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梁上的木纹果然盘盘绕绕,深的浅的交叠着,像把老骨头里的劲儿,藏得深,却看得清。他又低头画,铅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把自己的影子也描进了画角——短头发,厚卫衣,影子被日头拉得长长的,跟碑刻的影子挨在一起,倒像是新时光跟旧时光碰了面。
日头偏西时往小吃巷钻,摊主们早都支起了布帘,布帘是新洗的,蓝底白花,布纹缝里还带着皂角香,风一吹就鼓起来,像朵飘着的云。雪梨川贝羹摊子旁,摆着个铁桶做的糖炒栗子炉,摊主正用长勺翻炒栗子,“哗啦哗啦”的声响混着焦香,勾得人脚步都慢了。瓷碗在温水中浸着,碗边凝着串水珠,拿起时“啪嗒”一声掉在案板上,溅起小水花。阿叔系着藏青围裙,舀起一勺雪梨羹往碗里扣,雪梨块在碗底堆出小尖,又往上面撒了把碎枸杞,红的白的衬着,看着就喜人。我挖一勺往嘴里送,甜羹在舌尖化开时,暖意顺着喉咙往下钻,甜得清清爽爽,川贝的微苦跟着冒出来,倒把甜衬得更透,连牙根都浸着润。
转去老供销社旧址,内里改成旧物铺,木货架上摆着玻璃糖罐,罐中水果硬糖裹着透明糖纸,日光下闪着细碎星光。老板娘拿半秃的鸡毛掸子仔细扫货架,见我盯着糖罐笑,眼角弯成月牙:“小时候偷买这个藏在口袋里,化了后黏得满手糖渣,还怕被妈妈骂。”“刚煮了汤圆,要不要尝一碗?”她转身从里屋端出一碗热汤圆,白瓷碗里的汤圆冒着热气,糖水里还飘着几片桂花,“这桂花是去年晒的,加进去增点香。” 咬开汤圆,黑芝麻馅流出来,甜得恰到好处,混着桂花的香,让人想起小时候蹲在供销社门口等大人的时光,阳光暖,风也软,连等待的光阴都成甜的了。
古城初冬,日头柔润带温。风裹着甜羹、烤薯、栗子的香气与烟火笑语,砖缝草绿,梅香绕柱,寒鸦偶鸣,聊闲话的老人把日子过成慢火汤,暖透心意。
行至牌坊下,回头一看,古城浸在暮色里,青瓦苔痕显深褐,檐角铜铃轻摇晃。老榕树的影子铺在青石板上,晚归人踩影而行,手中揣着热乎吃食。花生糖的甜香混烟火味散开,这古城从不是冷硬的老玉,是活的、热的,揣满暖心事,被柔软的暖阳裹着,慢慢地晃进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