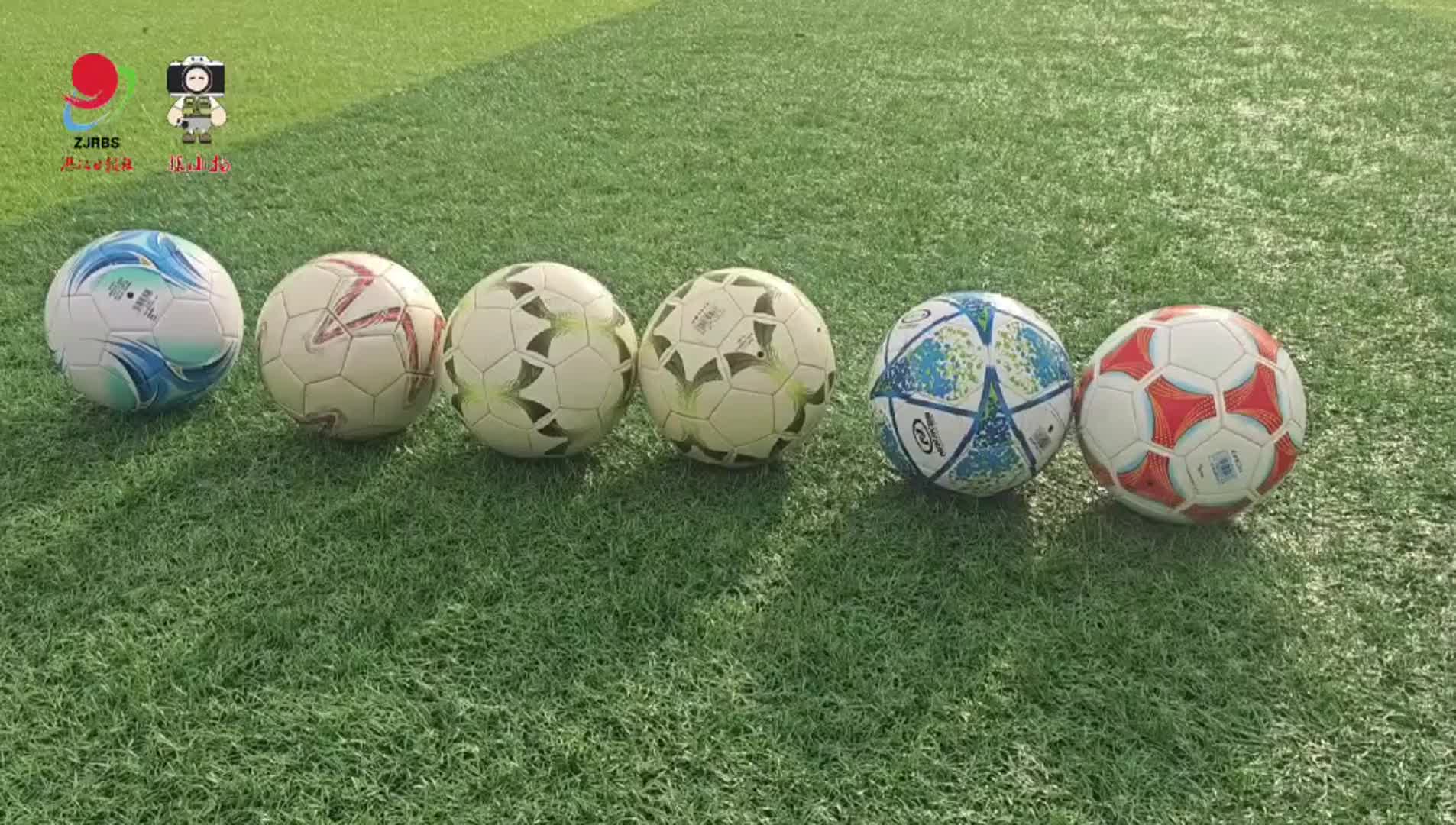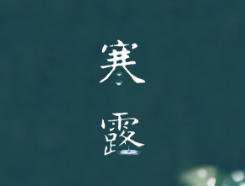一阵秋风,一阵秋雨,山一程,水一程,时间紧赶慢赶的脚步,渐渐地滑向寒露节气,滑向秋的更深处。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露水增多,且因气温较低,露水即将凝结成霜。自此,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寒露时节,北方即将进入寒冷的冬季。而南方,此时呈现出一派秋高气爽、风清日丽的秋景。
乡村寒露的秋色就像一幅油画。桉树林依然披着常绿的外衣,但边缘的叶子已泛出淡淡的锈红。村口的老榕树依旧苍翠,只是气根在凉风中轻颤。山坡上的乌桕树却最懂秋意,叶片由绿渐黄再转绯红。野菊花一簇簇绽放在墙角路边,金黄的花瓣带着山野的倔强。归鸟的剪影掠过竹林,溪水比夏日瘦了些。此时,不妨停下脚步,听秋风穿过竹林的低语。
寒露时节,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走进绚烂缤纷、萧瑟清冷的深秋。张九龄笔下的“寒露洁秋空,遥山纷在瞩”,以及韩愈所描绘的“新开寒露丛,远比水间红”,让我们感受寒露时节美丽独特的秋景;而李郢的“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则引起了我们思乡的共鸣;元稹的“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惹人对季节变化无限感慨。
在我的家乡粤西乡村,质朴务实的农人们可没有时间伤春悲秋,他们的脚步坚定地踏在土地上,他们的目光热切地看着田地里的农作物,就像看着他们的孩子一样。他们用坚实的肩膀与有力的脚步,书写深秋更壮丽的诗行。此时的稻田像一幅巨大的渐变画布,从根部的老绿过渡到腰间的淡黄,再到穗尖那一点点羞涩的金黄。阳光扫过时,会泛起一片片金色的涟漪。稻穗变得饱满而密实,它们谦卑地低着头,腰身弯成了优美的弧线,仿佛在向大地致敬。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青草汁液和谷物清甜的香气,那是阳光、泥土和稻谷共同酝酿出的、独属于深秋的味道。父亲每天都会到稻田边看一看晚稻的生长情况。只见他弯腰一手捧起一串稻穗,一手小心翼翼地掐下一颗稻谷,再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一捏,坚硬的米粒会渗出乳白的浆汁。这“浆汁”是稻谷即将成熟的标志。父亲松了一口气,笑眯眯地说:“再过一段时日,便可以收割稻谷了。”在他的眼前,仿佛看到了晚稻丰收的景象。而我,站在父亲旁边,看着这片青黄相接的稻田,心里会生出一种安稳的期盼,仿佛已经闻到了新米煮饭时满屋的清香。
在菜园旁,不知父亲什么时候种下的香蕉树长成了一片茂密翠绿的青纱帐。一梳梳香蕉像一弯弯倒悬的新月,从墨绿色的巨叶间探出头来。它们沉甸甸地悬在蕉叶下,积蓄着深秋的阳光与甜意,只待采撷。父亲说,香蕉快成熟了,过几天砍下一大梳,让我带回城里吃。父亲种的香蕉,似乎一年四季都在丰收,让我常常能吃到。那种甜是踏实而治愈的,能给人满足与熨帖,也能唤醒我童年最甜蜜的记忆。
寒露与菊花,应是极相配的。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买一些荷兰菊回来,种在门前的庭院里。这些重瓣的荷兰菊品种繁多,有很多美丽而诗意的名字,如:宝莲灯、紫芙蓉、红水晶、粉如意、玲珑、吉祥……颜色也五彩缤纷,有粉红色、粉白色、橙黄色、紫色、深红色……这些美丽鲜艳的小菊花,把我家庭院装点得缤纷热闹。
寒露时,寒意初现,干燥渐起。母亲的重头戏,必煲润肺靓汤。一大早,母亲便捉了一只大土鸡来宰杀,熬沙参玉竹雪梨鸡汤。母亲说,沙参玉竹滋阴,雪梨润肺,煲出来的汤水最是清甜滋润。我和父亲从田里回来的时候,饭桌上早已盛着两碗热腾腾的鸡汤。我喝一口鸡汤,感觉一股醇厚而温和的鲜甜,在口中缓缓释放,一股暖意从舌尖一直到心里去。我想,这大抵便是母爱的味道。
寒露正浓,月色清冷如洗。家乡的寒露,不像北方那样有满山红叶的壮丽秋色,而是一种浸润在日常生活里的、细腻的季节转换。它藏在母亲煲的那一煲老火靓汤里,藏在清晨那一丝凉爽的微风中,藏在父亲慈祥的笑容里。这寒露的夜,是冷的。但这可亲的灯火,这浓浓的亲情,这即将丰收的大地,却给人间贮满了最深厚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