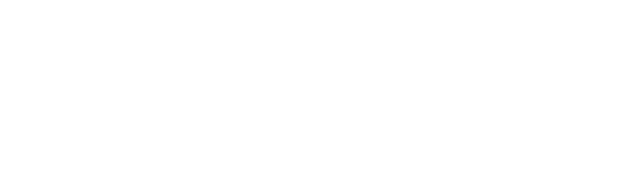整装待发。 万友 摄
整装待发。 万友 摄
窗玻璃上的雨痕还没干,绿皮火车就裹着岭南的潮气动了。1988年初秋,家乡连下3天暴雨,通往广州的公路塌方中断,这列绿皮火车成了我报到上课的唯一选择。攥着“湛江-广州”的硬纸板车票,辗转几趟班车才从农村到市区,指尖的汗粘湿了票边——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裤脚还沾着县道的水渍。
挤在人群里找座位时,鞋缝里卡着的泥点,是今早踩着积水赶车的痕迹;背包里装着母亲煮的茶叶蛋,蛋壳上还留着掌心的温度,是家人藏在细节里的牵挂;口袋里揣着面授通知,纸页边角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那时候的绿皮火车,像头喘着气的老黄牛,每走一步都带着“哐当哐当”的喘息;每过一个隧道,车厢里就会响起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像一群被雨淋湿的鸟儿在轻轻啼鸣;泡面的香气、阿婆怀里橘子的酸甜、潮湿空气里的泥土味,缠缠绕绕地揉在一起,成了这段旅程最初的味道——后来每次想起,都像回到了离家那天,母亲往我背包里塞茶叶蛋时,指尖触到的那抹雨珠的清凉。
那时的我,心里装着半是慌张半是期盼。慌的是长这么大,第一次上省城,像只刚学飞的雏鸟,不知道能不能在陌生的天空里站稳;慌的是暴雨打乱了坐汽车的计划,面对绿皮火车这陌生的“伙伴”,连怎么找座位、怎么接开水都一无所知;慌的是听说广州人多街道又复杂,怕自己到了那里会像迷路的孩子。盼的是从一些同事口中得知,广州有高高的楼房、宽宽的马路,能去那里上课,就像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新窗户;盼的是火车沿途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能遇见有趣的人,能把这段特别的经历,讲给自己的学生听。
出发前一天,父亲冒雨退汽车票,回来时裤腿卷到膝盖,浑身湿透。母亲在灯下收拾行李,叠好3件换洗衣,把茶叶蛋塞进保温袋。
湛江火车站的候车室不大,吊扇慢悠悠转着,空气里满是水汽。我坐在掉漆的长椅上,看雨点砸在站台铁皮棚上,“噼里啪啦”,像敲着节奏;落在铁轨上溅起水花,又被新雨覆盖;顺着窗户流下,画出弯弯曲曲的诗行。
检票时,人群像缓缓流淌的河水。走上站台,绿皮火车卧在雨里,车身绿得发亮,像洗过的翡翠,车窗如明亮的眼,有人探出头挥手。父亲帮我提行李到车厢门口,头发湿贴在额上,叮嘱 “注意安全”。火车开动,我趴在窗边,见父亲站在雨棚下,两眼望着火车,雨打湿了他的衣服,身影渐渐缩成黑点,我把脸贴在微凉的玻璃上,心里又酸又暖,
邻座大叔是个农民,黝黑的手布满老茧。他笑着指窗外:“这绿皮车慢,却能看够风景。”我望去,暴雨后的田野格外清新:甘蔗林叶子绿油油,稻田禾苗快抽穗,风一吹像波浪;村庄笼在薄雾里,白墙黑瓦若隐若现,农民披着蓑衣劳作,白鹭掠过水面激起涟漪。火车经小村庄站台,虽只停一两分钟,却见有人提篮卖水果,吆喝声随风飘进车厢;有人背书包跑向火车,卡通挂件晃来晃去;有人挥手递特产,满是牵挂。
车厢连接处最热闹。卖玉米棒的阿姨推着小车,铁桶冒热气,湛江口音拖得长长:“5毛钱3条,热乎的!”我买了3条,香甜糯滑,暖意从嘴里流到胃里。穿校服的学生趴在栏杆上写作业,铅笔“沙沙”作响,偶尔抬头望窗外,眼里满是对远方的期待。那时一般人没有手机(大哥大),有人看书,有人聊天,有人盯窗外发呆,看甘蔗林掠过,夕阳染红河天,云朵变成棉花糖,时光都慢了下来。
半夜,火车在小站停下,广播说铁轨因暴雨出故障。车厢里渐起烦躁,有人踱步,有人抱怨。邻座阿婆掏出褪色的收音机,粤剧唱腔飘出,像清泉抚平焦躁:“听听戏,别急。”她又拿出自家做的芝麻饼,分给众人:“尝尝,有点硬,却香。” 我咬一口,芝麻香里带着阳光味,想起母亲也常做这饼,每次出门都装一袋。慢慢地,有人跟着哼唱粤剧,有人分享零食,有人聊家常,气氛又热闹起来。
后半夜,我靠在椅背上,“哐当哐当” 的车轮声像催眠曲。偶尔被汽笛声吵醒,见站台上昏黄的灯光如温暖的星,有人匆匆上下车,小贩手电筒的光在黑暗里晃动。一次,我见一位姑娘在站台送别男友,两人牵手,姑娘眼泪掉在男友衬衫上;火车开动,男友追着跑,喊“等我回来”,姑娘站到火车成黑点,才擦泪转身,身影在灯光下格外孤单,我忽然想念父母。
清晨,火车到广州站。阳光驱散潮气,天空蓝得像干净的布。我跟着人群出站,看高楼直插云霄,汽车来来往往,商店招牌五颜六色,行人脚步匆匆,陌生又兴奋。后来常去广州上函授课,我又坐过几次绿皮火车,每次都想起1988年的雨天旅程:大叔的笑容,阿婆的芝麻饼,父母的挥手,“哐当哐当”声,成了老朋友的问候。
广湛高铁已经开通,湛江到广州只要1个半小时。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那张硬纸板车票,小字迹模糊,“湛江-广州”却清晰。边缘被摩挲得发软。我把它放在手心,仿佛又听见绿皮车的汽笛,看见窗上的雨痕。
绿皮火车载着雨与回忆,驶向时光深处。或许以后多坐高铁,但我仍盼再见那抹绿——它载着青年的求学梦、家人的牵挂,还有雨里的温柔与感动,像窗上的雨痕,虽会干,却永远留在记忆里,轻轻一碰,就会想起那段雨里的旅程,想起那列载着梦想与温暖的绿皮火车。